学术研究
前沿动态
序 即哲学史研究做中国哲学
发表时间:2020-04-17 21:20:38 作者:邹晓东 来源:
【书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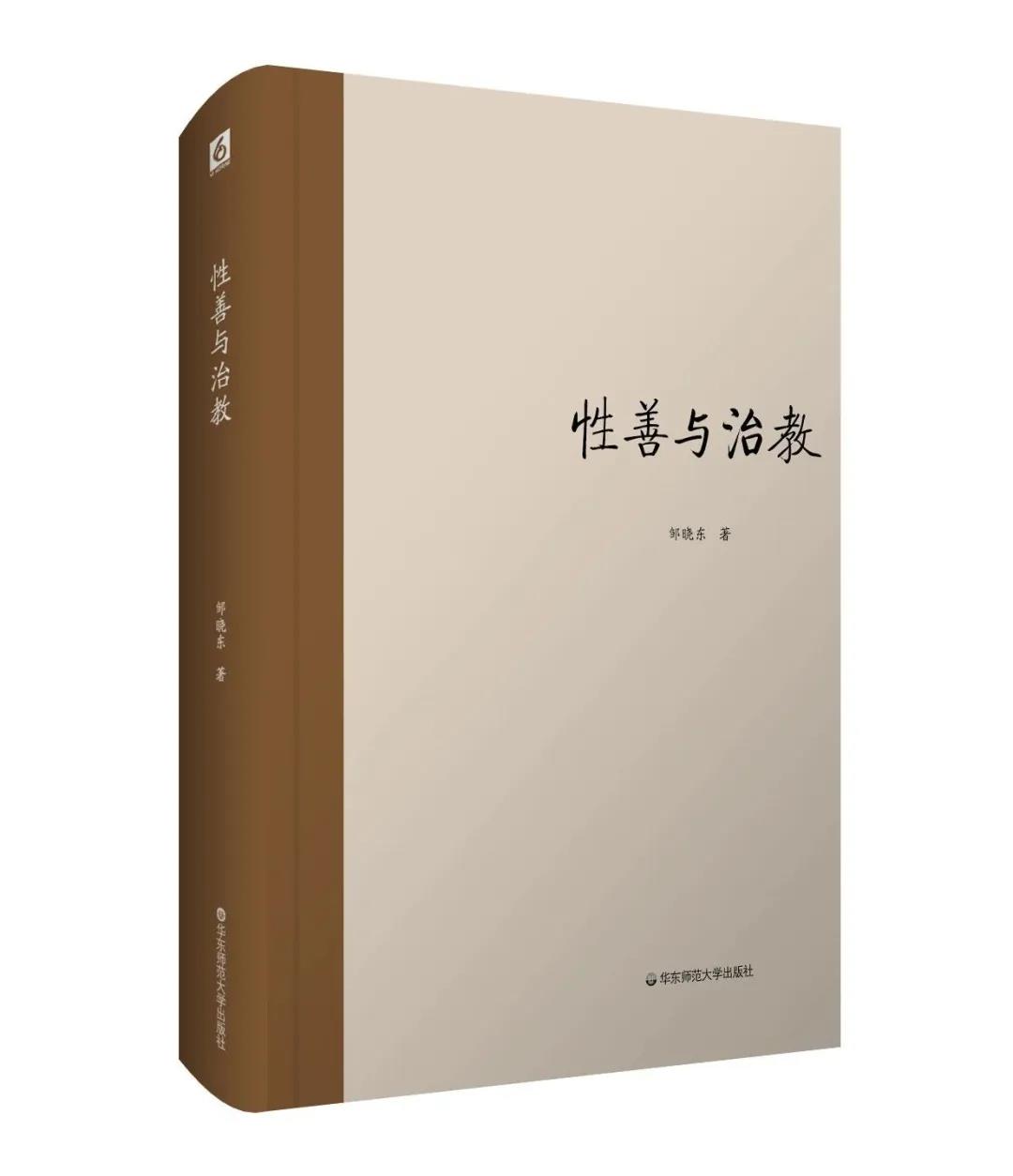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暨《文史哲》编辑部 副教授 邹晓东 著
《性善与治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即出
本文系该书序言
究竟该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史)?当今汉语中国哲学(史)界,对此一直充满分歧和迷惘。作为本学科的奠基人,冯友兰先生“三史释古今”的做法延续至今,直接造就了强大的“历史考释与思想观念复述”阵营(尽管当代的“复述”难免要受“西哲”渗透);其“六书纪贞元”的精神,则在南方学派“做哲学”“出思想”的追求中,有着更自觉的体现(尽管也可以“做”得“很中国化”)。但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表述方式”等问题的探讨缺乏长足进展,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者为了追求“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与特质”而倾向于抵制“西方哲学渗透”的大背景下,从冯友兰先生那一代学人延伸而来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这两种中国哲学(史)研究路数颇有被日益对立起来之势。
按理说,“即哲学史研究而做哲学”应该是最理想的模式——除非我们真的想把中国哲学消解到文史专业中去,或者我们真的自信哲学研究可以抛开历史遗产而平地起高楼——爬到思想巨人们的肩膀上,并且继续向前看,这才是继往开来的正道所在。然而,怎么爬,怎么看?是先爬再看,还是边爬边看?这同样也是问题。特别地,一入“史”门深似海,这里总有无穷无尽的与哲学思想的产生与传播相关,实际上却又“不那么哲学”的议题,在不断分散着原本“为了哲学而历史”的研究者的注意力(史学兴趣干扰了哲学性研究)。更何况,那些确实与哲学思想内在相关的历史问题,如《大学》《中庸》分别属于儒门中的哪一派,则往往又无法在对相关文本进行哲学性研究之前,给出任何有意义的回答。既然如此,有志于“即哲学史研究而做哲学”的研究者,便须不断反省何为“哲学性”,并通过这种反省不断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史料中的哲学性议题,以此来确保自己的哲学史研究不失其哲学性。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正想这样努力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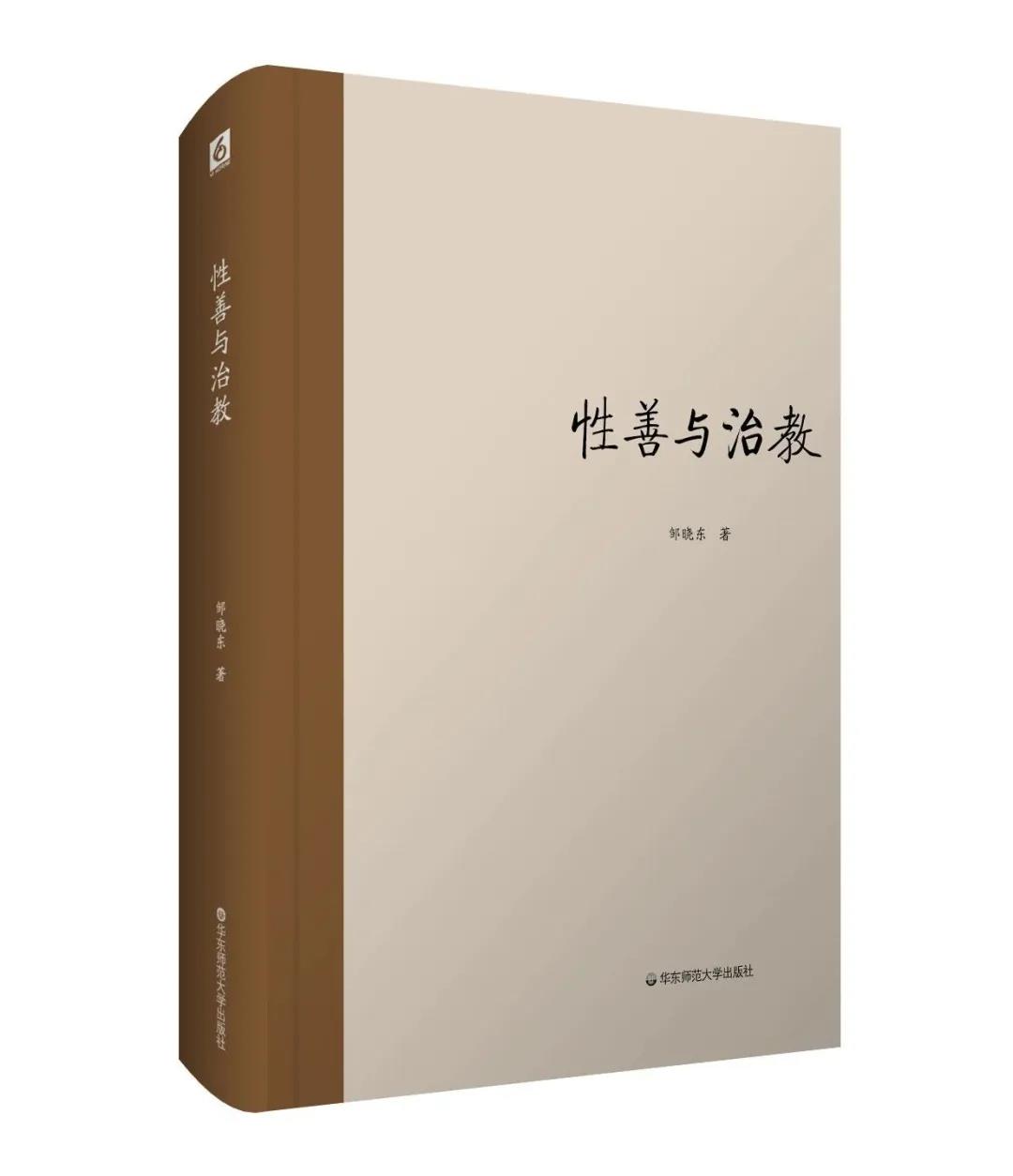
(邹晓东:《性善与治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邹晓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
此前(2018年9月),笔者已经出版了《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一书。眼前这本小册子在素材和思路上与前书既有重叠,亦有突破,在写法上则更加平铺直叙(而非将长程的哲学史心得,曲折地塞进《学》《庸》研究的小空间中),故更像一个“即哲学史研究而做哲学”的作品。本书的哲学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在导论中,笔者将本书标题中的“性善”与“治教”,奉为“儒学中的两种基础性生存意识”。“哲学性”正系于此所谓的“基础性”——那么,“基础性”又何所谓呢?
了解当代西方哲学动态的人知道,“基础性”连同所谓的“还原论”一度成了分析哲学研究中的显学——“基础主义”是也。但在普兰丁格(Alvin Carl Plantinga)等人的攻驳(其核心指控是:表述基础主义的命题,本身都经不起所谓的基础主义的推敲)下,这种“基础主义”目前已基本丧失立足之地。故此,笔者所谓的“基础性”不是“基础主义”意义上的基础性;在本书的词语用法中,某议题具有基础性是指:总要追究到这个议题上去,该议题在根子上无法回避。从形式森严的基础主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回归到“总要追究到这里,在根子上无法回避”的日常语言,这一点儿都不会伤害我们对哲学性的追求。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包括儒家哲学人)固然锻造出了许多艰深玄妙的概念用来论述各种基础性议题,但平心而论,基础性议题之所以基础全因其是严于思考之人所无法逃避的生存攸关的根本问题(否则,人总有理由将其搁置,甚至压根儿不会思及,这种可有可无的议题当然不具有基础重要性)。就此而言,哲学上的基础性议题,盖无不可以用平易近人的“大白话”通俗易懂地表述出来。否则,通俗之人岂不恰恰足以绕开哲学,并用此绕避证伪哲学学科的基础性,乃至严肃地将哲学定性为一小部分人的偏执病?!
“性善与治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与‘遵从外在权威的指导’”。这确实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但在立论和实践中真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却又殊为不易。主张“遵从外在权威的指导”者,即便名义上是坚定的性恶论者(接受外在指导的必要性被认为正在于性恶),常常也还是不得不变着花样承认人心固有知善的能力(这正如梁涛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荀子人性论具有“性恶、心善”双重结构),否则外在指导不可能进入被指导者的脑与心;提倡“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的性善论者,则因为自己毕竟也是在特定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故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特定说教的推崇,以及对权威的施教地位与施教手段的切慕(如本书第二篇所指出的,“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在思维方式上已然踏入了“外铄”论的门庭)。可以说,围绕着如何安排“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声(性善—率性)”与“遵从外在权威的指导(治教—受教)”这两种基础性生存意识,儒学史既表现出了“对立阵营激烈交锋,乃至水火不容”的态势(“孟荀之争”“孟荀二分”),又时常展现出“一方自觉不自觉地兼容或变着花样地增设对方所推崇的基本预设,不惜由此破坏乃至颠覆自己的固有立场”的难舍难分格局(“孟中有荀,荀中有孟”)。总之,“性善与治教”议题在儒学史上非常基要,相关的论争与辨析场面十分复杂!
为避免同行讥议,本书主体部分没有采取中西比较的研究路数。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在本序言中冒昧地强调:“性善与治教”这一议题,具有世界性的哲学意义。参考基尔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代表作《哲学碎屑》中的“两希”比较,可以说:儒学中的“性善—率性—自作主宰”意识,与主张“灵魂固有真理,学习就是自我回忆”的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回忆说”,在根本上相通;而“遵从外在权威的指导”的“治教—受教”认知模式,则只有强化为“真理教师”认识论,才能与“自作主宰”“自我回忆”的自主模式,实质性地拉开距离。“性善—率性”与“治教—受教”,或“苏格拉底模式”与“真理教师模式”,堪称仅有的两种认识论逻辑。这种可比性意味着,中国传统儒学资源,完全可以经由对“性善与治教”议题的深度研讨,大举进入世界哲学的腹地。
顺便一提,2018年在中国北京召开了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其主题“学以成人”曾在网络上引起诸多非议。在笔者看来,造成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非议者们盖只知道《大学》或《荀子》式的崇尚外在权威的“治教—受教”之“学”,而不晓得在《孟子》与心学当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其珍视学者个人内在呼声的“性善—率性”之“学”,遑论将这两种“学”与作为西方思想双源头的“两希”之“学”进行长足的比较与会通研究。尽管本书主体部分没有直接进行这种比较会通研究,但我还是想说:对“性善”与“治教”这两种基础性生存意识在儒学史上的出现、互渗、分离、统合的历程做框架性考察,醒目地标示出贯穿其中的“真知”问题,进而站在所考察的儒学传统中的思想巨人们的肩膀上展望“真知”问题的更佳处理方案——长远来看,这种“地方性”研究势必将会增进世界哲学的福祉。至于本书究竟能为此福祉的增进做出几分贡献?这只能交给读者们去不断检验。
最后简介一下本书的体例。本书导论(尤其后两节),是对正文三篇中的思想心得的进一步提炼。但导论与正文三篇中的每一篇,作为论文又均显得篇幅过长,不利于读者迅速把握通篇的架构与主旨。鉴于此,笔者专门花了点心思,为这四篇文字分别撰写了引言和结语,置于每篇的开始和末了;后又在本书的跋中增设了“杀青卅四论题”,力图集中呈现本书的框架与脉络。读者也可以先行浏览这些概述性文字,先对全书内容有一粗略的了解,以便更高效地把握书中一波三折的具体分析与论述。
诚盼广大的读者同仁,不断地有教于我!你们直言不讳的点评与批评,必将成为我阶段性地反思自己的总体视角、研究路数、具体观点,从而以更好的姿态去进行下一场角力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