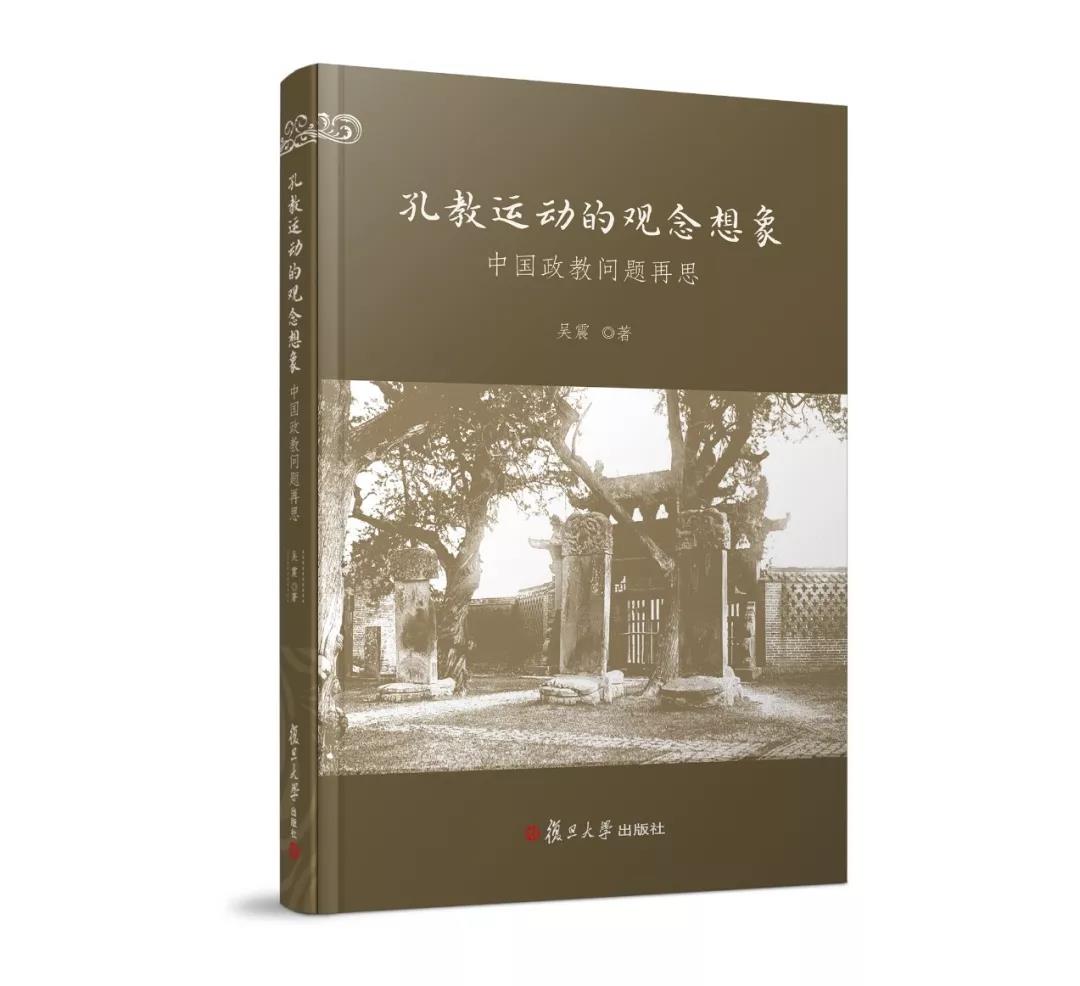学术研究
前沿动态
【新书推荐】孔教运动的观念想象:中国政教问题再思
发表时间:2019-03-06 18:55:48 作者:吴震 来源:
作者:吴震 著
ISBN: 978-7-309-13967-9/D.959
开本: 32 开
装帧:精装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ISBN: 978-7-309-13967-9/D.959
开本: 32 开
装帧:精装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本书封面图片为即墨孔庙遗址。1898年年初,发生德国士兵毁坏即墨孔庙的事件,激起当地士人以及全国其他地方士人的抗议和声援,继而引发了第二次公车上书,成为触发戊戌变法的一大诱因,而变法运动又衍生出一场声势浩大的孔教运动。这一连串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历史事件竟与即墨孔庙有着微妙的关联。
作者简介
吴震,江苏丹阳人,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日本国际井上圆了学会理事,曾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等职。主要专著有:《阳明后学研究》(增订版)、《罗汝芳评传》、《泰州学派研究》、《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繁体版、简体版)、《〈传习录〉精读》、《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儒学思想十论——吴震学术论集》、《东亚儒学问题新探》、《朱子思想再读》等;编著有:《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等。
内容简介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中国经历了戊戌变法、孔教运动、共和立宪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社会事件,在这场社会转型的约三十年间,由各种“主义主张”“问题符号”激起的“思想战”此起彼伏,在此过程中,“孔教”问题始终隐伏其中。参与“孔教”论战的双方主要在争执两个问题:儒教(孔教)是否是宗教?共和政体是否需要宗教意义上的儒教?但在此背后存在一个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是:应如何处理“政教”问题以重新安排中国社会政治秩序。
近年来康有为的“符号化”与政教问题的凸显乃是本书的一个问题切入点,“政教问题”在当下中国何以重新出场等学术现象的确令人深思。本书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有关政教关系问题的考察,特别对朱子、章学诚等人的儒家政教观进行了梳理和澄清,进而对康有为推动的孔教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康氏表面上认同近代西方“政教分离”的立国原则,然其政教设想的实质在于重构“孔教国教化”,其结果便不能保证在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前提下,保持宗教在精神领域的独立性,更无法合理安排由近代跨入现代的中国政教秩序。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不久,便在政教问题上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坚持“分则两美,合则两伤”的政教观,晚年思想立场更趋近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儒家主义正合乎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故不妨以“近代新儒家”来为他进行历史定位。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善待儒教?如何构建合理性的“宗教中国化”等问题?这是吾人面临的时代课题,值得思索。
推荐语
中国近代所谓“政教”问题应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是否适合用“政教合一”的一元论来把握,康有为的政教论述及其孔教论应如何加以认识,这些问题晚近颇受关注。本书对此提供了一个焦点集中的研究,作者思想史的视野宽阔,富于当代的文化意识,论述深入有力,对推进这一主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来
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在体制与观念两大层面发生了激剧的转变,近代儒家面临如何应对西潮冲击以解决“政教”秩序的重建问题;然此一问题在当今却被重新点燃,引发人们对儒学现代性命运的沉思。吴震教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宽阔的理论视野,对近代中国孔教运动所凸显的政教问题予以清晰有力的思想辨析,启人省察、颇值品味。
——郭齐勇
政治与教化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吴震教授此书以朱子、章学诚的皇极、政教合一论,康有为孔教论为线索,揭示了儒家秩序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及面对现代性挑战所出现的矛盾和困境。其世界性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理清中西政教关系的同异;其现实性的关切,刺激人们探索现代儒家发展的可能方向。
——干春松
导言:康有为的“符号化”与政教问题的凸显
近代中国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不久而兴起的“洋务运动”也的确表明古老帝国的脚步正在跨入“近代”,意味着中国被卷入全球“现代化”(韦伯语)的进程之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思想便不得不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不过,思想观念的更新往往滞后于时代社会的变迁,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观念转向的真正启动,则肇端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以及稍后的那场持续仅“百日”的所谓戊戌变法运动。
当然,从广义上说,“洋务运动”便是一场从体制内追求“自强”“富国”的一场漫长的“自改革”(龚自珍语)运动,只是这场发生于1998年的短命而亡的戊戌变法却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至少表现出两个重大的后果: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已难以维持“前现代”帝国政经秩序的常态而开始分崩离析,从而引发了空前的中国政治秩序危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的伦理纲常开始遭到普遍质疑,随着“冲决网罗”(谭嗣同语)的呼声日渐高涨,进入了思想上“怀疑一切”的时代。
可以说,自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一直到“后五四”时期的1920年代的约三十年间,对中国而言,不仅是社会转型期,更是观念变革期;无论是政治上或文化上的激进者还是保守者,人们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时代焦虑:觉得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制度还是教化、道德还是器物等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围绕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问题爆发了激烈的“思想战”(杜亚泉语),导致“问题符号漫天飞”(蒋梦麟语),五四之后,胡适(1891—1962)更是直呼中国进入了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甚至以为这八个字才是对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时代的“最好解释”。
另一方面,自1890年代“后洋务运动”以来,以“保国”“保种”“保教”(语见张之洞《劝学篇》)的三大口号为标志,文化上的保守派以及政治上的维新派等各种势力及其种种主义主张就已呈现纠缠交错的态势。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1858—1927)倡议重建“孔教”,以为由此可以在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可以一箭双雕,一并解决“保国”与“保教”的问题。即便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与创建共和之后,康氏一方面主张以“虚君共和”对抗“民主共和”,一方面仍不放弃树孔教的理念,鼓动其弟子陈焕章(1880—1933)于1912年底建立了全国性的“孔教会”组织,随后便发动了两次(1913年和1916年)向国会要求立孔教为“国教”的所谓立宪运动,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由于民国之后袁世凯(1859—1916)和张勋(1854—1923)的先后两次帝制复辟均对孔教会势力有所利用,更使孔教运动“身败名裂”。与此同时,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便以批判康有为孔教思想为突破口,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在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也增强了批孔的火力,从此康有为等孔教会势力被视作旧文化、旧时代的代表,再也无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新出场。
可以看到,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在各种“主义主张”“问题符号”激起的“思想战”此起彼伏的历史进程中,“孔教”问题始终隐伏其中。表面看,参与“孔教”论战的双方在争执两个问题:儒教是否是宗教?共和政体是否需要孔教?然而事实上,在孔教问题的背后存在一个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处理“政教”问题以重新安排中国社会政治秩序。
本来,“政教”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无非是指政治与教化,两者并不构成严重的冲突关系,因为儒家既非严密的制度宗教,更无教会组织,国家体制虽呈现为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之形态(尤以明清时代为甚),然而朝廷的政治权力与儒家士人集团处在一种互相利用又彼此制约的微妙关系当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断然打破这种平衡以求单独的发展,也就是说,政治与教化的互相兼顾才能使整个社会秩序得以平稳的延续。只是到了19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时代,在西化思潮的不断冲击下,随着各种外来的政治学说、宗教势力的广泛渗入,政教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微妙而又重要的转变——即在近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与宗教究竟应当互不干涉还是应当携手合作?不少士人精英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不行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宗教信仰,故应模仿西方宗教传统也在中国重建制度性的宗教,以为由此就可改善整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而增强抵抗外来帝国势力的机制。于是,政教问题陡然成为与文化革新、体制变革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议题而广受关注。
而在当下中国的改革运动得以全面深入之际,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开始受到正视和关注,于是,否定传统才能步入现代的所谓启蒙情结值得深刻反思,换言之,人们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并非是格格不入的,那种以为传统必阻碍现代发展的思想怪圈必须打破,从而回归传统文化的呼声在社会各界此起彼伏。在这股传统文化热的背景下,有不少学者开始将眼光投向清末民初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有关政教问题的大讨论,进而发现一百二十年前的改革“先知”康有为竟有许多政教主张可以在当下社会被重新激活,出现了康有为被“符号化”的奇特现象。于是,政教问题——即所谓政治与儒教、制度与儒学如何平衡等问题的探讨也在随之升温,而且相关讨论似已不能满足于历史性的描述而应进入理论上的重建,甚至出现了借康有为之“酒”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现象。然而稍作省思即可发觉,其实作为“符号”的康有为已被抹上各种“颜色”,而其思想“本色”却反被遮蔽。
因为,究竟何谓“政教”?政与教的关系究竟应如何调适?康有为借助“孔教”运动欲重构未来中国政教秩序的内在思想机制及其最终理论企图又究竟何在?这些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然而说实话,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严密的学术探讨并非易事。我们的讨论将建立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基础之上,但目的并不在于有关政教论述的历史重建,而是采取一种描述性的策略,对历史上各种有关“政教”问题的论述特质以及当今学界对传统政教观的各种辨析乃至主张做一番历史学的描述,同时,针对相关问题也作出必要的理论省察;至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未来走向,则需要今后学界展开深入的理论反思和理性判断。
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是由一篇长文扩充而成,该文原题:《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教关系”问题——以反思康有为“孔教”运动为核心》,现将该文的“摘要”略作扩充,附在“导言”之末,或对读者了解本书撰述之旨意及其思路有所帮助:
近年来,“政教”问题成了学界的一个热点,引人深思。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孔教运动的赞同者或反对者都面临一个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政教问题以重建中国政教秩序?依西学,“政教”系指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历史上有“合一”或“分离”等各种政教形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教是指儒家教化系统而非严格宗教,公羊学所言“布政施教”盖谓政事与教化的安排,因而英文Caesaropapism(意谓“恺撒与教皇的合一”)所表达的“政教合一”并不能照搬过来置入中国语境。即便在近代西方,“政教分离”已成为建构民族国家之政治前提,然而在“政教分离”原则之下,仍然存在各种不同的形态,既有积极的作为“建构原理”的政教分离形态,偏向于中立的宽松主义,又有消极的作为“限制原理”的政教分离形态,偏向于严格的分离主义。故不可一概而论。在中国历史上,公羊学首倡“政教之始”之观念,而公羊学俨然成为近代中国各种变法主张以及康有为孔教思想的重要资源,值得关注。
然而近年张灏撰文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教问题表示了重要关切,他通过对朱子《皇极辨》一文的前后两个刻本的仔细解读,发现朱子晚年思想由政教二元向一元发生了转化,由此断定朱子所追求的是三代社会政教合一的理想形态;基于此,张灏强调任何以政教一元论或二元论来涵盖整个中国历史都有可能失之武断。无疑地,张灏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只是其对朱子文本的解读似有失误,故而值得重新探讨。事实上,以朱子为代表的道学家高举“天道”的旗帜,要求君臣共同遵守,因为道统在政统之上,政统须以遵从道统为前提,这就说明儒家政教观并不是一元论的立场,而是表现为二元论下的政教依赖之形态。在秦汉以降的中国历史上,明确主张回归“官师政教合一”的先秦传统则非18世纪清代中期史学家章学诚莫属,显示出其政治立场偏向于国家威权主义,只是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在乾嘉时期尚乏人响应。
不过,到了道咸之后的晚清时代却时来运转,赢得了魏源、龚自珍等士人精英的积极回应,而政教问题更是急速升温。戊戌变法之际便提出孔教主张的康有为更是以重建政教为核心问题,只是在具体策略上,他却主张不妨因应时代潮流,采取“政教分离,双轮并驰”的立场,表明其孔教主张并不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而且他坚信与“政教分离”相配套的“信教自由”之观念原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儒释道回”各尊其道、相安无事的历史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故而孔教国家化既是重建传统,同时又能顺应世界新潮流。但须指出,康氏孔教之论旨在将儒教向国家宗教的方向扭转,其结果必带来文化专制的负面效应,遂使“信教自由”变成一纸空文,特别是在帝制已然崩塌的背景下,仍抱守残缺,欲变世俗儒教为国家宗教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了。
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甚至尊奉康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然而就在戊戌失败而流亡日本之后,很快他就借由日本接触到西方有关“政教分离”问题的新知识,意识到这一近代国家的建国原则远非康有为孔教思想所理解的那样,于是,在1902年他便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在政教问题上公开表示与康氏分道扬镳,自此之后,他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解再也没有改变其立场;同时,他开始转而关注“公私两德”的道德重建问题,主张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一场“道德革命”,并且认为培养“私德”才是重建社会“公德”的基础,表现出“近代新儒家”向传统文化的复归立场,体现了重在调适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风格。
及至当代新儒家,例如五十年代后“花果飘零”至港台的新儒家与当时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者之间竟然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问题也有过种种观点上的碰撞。以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坚定认为政教合一是保证古代中国“天子制度”之合法性的观念基础,故而政教合一体制“在传统中国从未崩溃”;与此相反,当代新儒家如徐复观等人则坚定认为,官师合一为特征的“政教合一”是比专制主义更为“专制”的政治主张,是“儒家绝不能加以承认”的观点。甚至有当代儒者认为,由于“政教合一”属于西方语境下的特殊用语,因此任何企图以此观念模式来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努力都属于“食洋不化”之举,不值一谈。
当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这场论争的是非对错姑当别论。要之,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从“近代新儒家”到“当代新儒家”之所以对政教问题始终不能释怀,充分表明政教问题是儒家文化在面对如何重建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之际必须做出回应的重要课题;而在我们看来,这同时也是为了应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亦即如何在当下中国通过创造性转化来善待儒家的社会教化意义?这应当是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未来走向之际所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